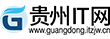人生若觉不快乐,只因未读苏东坡
我初识东坡,是从他的一阕词开始的。那时刚升上初中一年级,开学不久,教语文的龙老师突然辞职了,新来的程老师第一次上课,刚好在中秋节前几天。她讲了些求学台湾的故事,然后在黑板上写下一阕词,简单讲解了内容,说是和中秋有关的,我默默抄了下来。回家途中读了几遍,第二天就会背了。我生平诵读的第一阕词,就是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我记得当时对词意本身并没有很了解,但在朗读中却有着莫名的感动,仿佛内心深处有些情绪被挑动了起来……
在那十来岁的青涩岁月里,我陆陆续续地又读了些词:苏东坡、辛稼轩、李后主、李清照、柳永、秦少游、周邦彦……随兴地选读背诵,似懂非懂的感受,读得不算多,也没什么条理,却总觉得其中有着似曾相识的心情。
 【资料图】
【资料图】
然后,我来到了台大,走进中国文学世界,用心地阅读诗词古文,在历史和思想的典籍中沉思,也在古今中外的作品里探索。慢慢地,我发现深入的阅读使我能面对作者、面对作品,也透过他们面对了自己,进而唤起了自我的生命意识,重新认识自己,并在其中成长。
这样的过程,交织着许多作者、作品和不同时期的自我。而中间不时出现、最终影响我最多的,是那最初牵动我少年情怀的东坡及其词。
林语堂《苏东坡传·原序》说:
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浓、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他一直卷在政治旋涡之中,但是他却光风霁月,高高超越于苟苟营营的政治勾当之上……他能狂妄怪癖,也能庄重严肃,能轻松玩笑,也能郑重庄严,从他的笔端,我们能听到人类情感之弦的振动,有喜悦、有愉快、有梦幻的觉醒,有顺从的忍受……肉体虽然会死,他的精神在下一辈子,则可成为天空的星、地上的河,可以闪亮照明、可以滋润营养,因而维持众生万物。
的确,苏东坡是中国文学世界里最耀眼的星光,历来最受欢迎的作家。读者普遍赞叹他的才华,爱听他的逸闻趣事,欣赏他的生活态度,同情他的际遇。许多人反复阅读他的作品,吟哦记诵他的诗词文句,觉得因此可以让自己多一点面对挫折的勇气,甚或能够安下心、定下神来,感受到生命中闪烁的爱与希望。
不过,并非人人都爱苏东坡。在宋代像何正臣、舒亶、李定之流,故意曲解东坡文字,罗织罪状,欲置他于死地,应该是最讨厌甚至否定东坡文学之一群。当然,这里头牵涉到的是政治因素、功名利益——忌恨、恐惧往往令人远离文学艺术,看着耀眼的光彩也尽成难以忍受的芒刺。此外,从宋代开始,许多道学家就不喜欢苏轼,嫌他学问驳杂不纯,如纵横者流。《朱子语类》中记录朱熹批评东坡之语甚多,说他“气节有余”,却是“放肆”、“天资高明”、“善议论”,然意多“疏阔”,并劝有才性的人,千万不要学坡公……这些论点至今仍普遍存在于学界。从某些角度来看,会感觉其中不免夹杂门户之见,但或许也更关涉到彼此人生理念不同、生命调性有异。只能说,天才型的创作者与严谨思考的学术人物本来就是两种很不一样的类型,难以相容。与其费尽力气分辨此中是非高下,倒不如互相尊重,各随所好就是了。
我们讨论东坡,首先需回到历史场域,看看他的处境和作为。以前杜甫曾说:“名岂文章著。”传统士人虽有“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认知,但仍多以事功为著。东坡自少即抱负澄清天下之志,入世情怀甚深,后来虽遇贬谪,但屡仆屡起。时人爱赏自己的文章,东坡应该会高兴,而作为一位自觉意识极强的作家,他对自己的作品自是“得失寸心知”。有人批评东坡有名心,但试问从孔子以来,中国读书人谁不在乎自己的名声?正因为在意美名,他们孜孜矻矻、夙兴夜寐,希望做点有益于天下的事,得到世人的敬重,“毋忝所生”,也无愧于天地。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引孔子的话“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正反映了他身体虽受凌辱摧残,此心依旧未死,犹相信生命的价值可于时间见证,世间自有公评。因此他能将心比心,对古人的际遇,有着同情的了解,编撰《史记》,替前贤立传,留给后人解读,并相信必有知音者。所谓名心,何尝不也是一种提振、策励生命的重要力量?它让人相信只要忠于自己,凭借砥砺德行,勠力从公,发愤著书,可立德、立功、立言,成就不朽的人生。不过,如果汲汲求名,却无真材实料,或是沽名钓誉,就不可取了。东坡并不是如坊间传说那样整天嬉笑怒骂,舞文弄墨,好像没做过一点正经事的风流才子。阅读东坡一生,除了文学成就,也不要忘了看他在朝、在野、在地方上的种种建树,以及他如何深受同僚敬重、百姓爱戴,这些都可以清楚地呈现他积极任事、认真生活的态度。可惜批评他的人,却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这些。
说东坡思想驳杂,缺乏高度与深度,乃学界常见的论点。世间的学理,不是大部分都要回应人生的问题吗?如果各种思想都可在一个人的心灵里,依违离合,不发生严重冲突,反而能融会贯通,能让人在进退出处间有所依循,安于所处,乐在其中,那不是很美善的事吗?东坡的思想,融合了儒家、佛学和老庄。他吸收各家思想的精粹,与实际生活结合,化为深刻自然的生命智慧,不尚空谈。他曾用龙肉与猪肉表明他的态度:“公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东坡的学问多切人事,他充满入世的情怀,总希望能将学思所得落实于现实人生。我就喜欢他那种合乎人情的思想,平易实践生命的态度。但我们也知晓,东坡绝非完人,他有优点,也有性格上的缺陷。论学问之渊博,天分之高,东坡于唐宋文人中实罕有其匹,可是他豪迈之气不能自掩,光芒四射,难免锐利伤人而不自知,因此常以文字诙谐开罪于人,屡遭贬谪,并不完全是因为政争的缘故。但是,人之可贵,就在有不完美处,让人有机会可加改善,得以学习成长,而那些勇于面对人性脆弱的人,才有可能于成败顺逆之际、取舍抉择之间显现其坚韧、良善、光辉的一面,开创更有意义的人生。东坡之受人景仰,不仅仅是因为他有令人难以企及的机智与才情,更在于他和我们一样会犯错,有缺点,但却比一般人更能承担苦难,并以乐观的精神、豁达的胸襟,面对人生困境,表现出更强韧的生命力。
我们尚友古人,因为古人有值得学习的地方。穿越时空,大家喜与东坡神交,简单地说,乃因他不是仰之弥高的那种典型,不至于让人“高不可攀”。东坡曾说,他可上交天子,下交乞儿。他喜欢老实一点、纯朴一点的人,而有真性情、真才学的,他尤其喜欢交往,至于刚愎自用、自以为是或假道学的人,则难免遭受他冷眼对待或言辞嘲讽。这种不够圆融的个性,过于天真、直率的表现,在政治上是会吃亏的。但我们为什么要容忍乡愿呢?对习惯忍让的读者来说,暗地里欣赏东坡的直言不讳,觉得痛快,让积郁的情绪得以疏导发泄,心里会舒服一些。至于对本来就不那么循规蹈矩的人而言,读到东坡的犀利言辞,自然拍案叫好,认为深得我心。要跟像韩愈、辛弃疾一类的文人交往,得忍受得了他们的头巾气、牢骚气。和李白、东坡在一起,自然轻松得多,有趣得多。李白豪情万丈,无拘无束,看着他痛饮狂歌,是一种过瘾,令人由衷地喜爱;跟着他寻欢作乐,自己也兴奋不已,一切苦恼霎时间都顿然消失。李白酬赠的诗篇特多,他对待朋友十分真诚。譬如说,“长风万里送秋雁”,如果你是那归去的雁儿,诗人愿化作万里长风来相送,你能不感动?如一阵秋风,李白自个儿来自个儿去,他爱交友但不喜欢太黏腻的关系,如浮云一般的潇洒,聚合随缘,在一起时彼此取乐,分散后也不必为谁挂心。比较起来,东坡温煦如雨后山头相迎的斜阳晚照,给人特别温暖而容易亲近的感觉。李白之情有点像酒,浓郁而强烈,令人醺然陶醉;而东坡之情则如茶,和润清淡中自有甘醇,可细细品味。东坡用情较深较广,但多情多感之人,苦恼的事也多。东坡之所以说“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那是他真实的体验。明知情感会带来身心创痛,但要他忘情、逃情,他却做不到。正因愿意承担,勇敢面对,“入乎其内”,才能淬炼出更坚强的韧力、更开阔的心胸,遂能“出乎其外”,创造更高远旷达的生命意境。东坡文学见证了他伤情、体情、悟情、适情的经历,于诗词文赋中各有体现,而在长于言情的词体中,尤能看见东坡多情生命里脆弱又坚韧的一面。其词所抒发的真情实感,借由激昂的文辞、幽咽的语调,抑扬跌宕,最易触动人心,与读者接近,并带来启发,引起共鸣。
林语堂说:“我们只能知道自己真正了解的人,我们只能完全了解我们真正喜爱的人。我认为我完全知道苏东坡,因为我了解他。我了解他,是因为我喜爱他。”他写《苏东坡传》,多少带有自我认同的意味。林语堂所向往的是艺术的生活,他认同东坡的,是东坡的自由精神和生活趣味。东坡的文学世界确实丰富多姿,由他的文学所折射出来的生命光彩也灿然可观,诗文辞赋各有风貌,更不用说文学之外的表现了。我也喜欢东坡,而多年来感受最深、了解最深刻的是他文学的一小部分——“词”。不过,词虽小道,亦有可观者焉。词之为体,原是配合歌唱的文辞,东坡虽借以抒发一己的情意,改变了词的抒情面貌,但他亦未完全破坏体制,反而充分运用词体的抒情特性,以某种特殊的文辞语态表达某种深切幽微的情思。经由词体,我们可贴近东坡内心世界最幽暗的部分,知晓他在时空流转中的忧恐与不安,碰触他生命底层最真实的一面。而且,我深信东坡填词自有独特的意义,他在词中流露的情感既真且切,更能呈现他人性中脆弱又坚强的实貌。因此,可以这样说,词乃了解东坡跌宕情意最具体又最深刻的一种文体。
(未完待续......)
关键词: